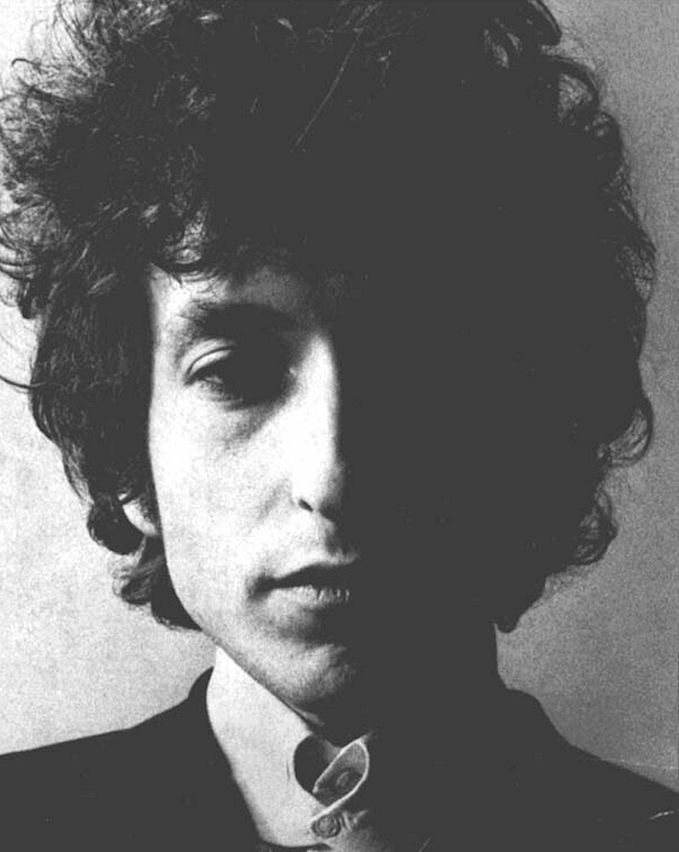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「性侵害案件被害人年齡與性別交叉統計」:2020 至 2022 每年的兒少性侵害案件分別為 5978、4520、4809 件,皆佔性侵害案件總數約 6 成。
也就是說,近 3 年以來,平均 1 天約發生 12~16 件兒少性侵害案件。其中,女性與男性兒少被害人的比例約為 3:1。而這些還只是「有通報」的案件。
那麼,什麼是沒通報的案件呢?我就是其中一例。十年以來,我守著「兒少性侵倖存者」的身分,任由它影響我生命的每個面向。
有人可能會說「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,馬上求救就好啦!在痛苦什麼?」
或是「辛苦你了,有這麼痛苦的經驗。可是,為什麼不曾嘗試求救呢?」
原因很簡單:求救的成本,非常、非常、非常地,高。
目錄
💠為什麼要講 ── 不知道什麼是「性侵」
💠講了誰會信 ── 當世界裂成兩半
💠講了沒證據 ── 舉證門檻高
💠講了被批判 ── 被冠上莫須有的責任
💠講了更痛苦 ── 每講一次,就挖深一次傷痕
💠結論:為什麼倖存者不願發聲?
為什麼要講 ── 不知道什麼是「性侵」
事件發生時,2014 年,我才七歲。我所受的性侵害防治教育,僅包含老師朗讀兒童讀本、帶我們認識身體紅綠燈、看經典影片《杰哥不要》等。
但對當時的我來說,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麼是「性侵」。
例如:很多人認為的:只有性交才算性侵,包含口交、陰道交、肛交、指交、器交等。但實際上,包含持續性的撫摸、舔弄等未侵入的所謂「猥褻」,在《刑法》上也是一種「性侵害」。
而我對此全然無知。更別提其他重要觀念:「蒐證」是被性侵時的第一要務,以及後續的主動和可信任的家長、老師、社工師等人求助了。
或許你認為:強化學齡前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就好了啊!可是,退一步來說:就算我知道這很重要,我可能還是不敢講。
為什麼呢?
講了誰會信 ── 當世界裂成兩半
當我一講,世界就會裂成兩半:相信我,與不相信我的人。
尤其是當我在網路上爬夠多案例後就發現,「不相信我的人」肯定會佔多數。畢竟,加害者可能是品性聲望都不差、有生產力、對家庭、朋友與社會都有貢獻的、深受信任的「好人」。
我要承擔這個風險嗎?在最壞的情況下,只有自己願相信自己的現實。
例如:在講之前,無論如何我都愛我的家人。然而,在講之後,如果家人質疑我、檢討我、不信我,就像許多兒少性侵倖存者經歷的那樣,我怎麼辦?
或許你認為:權益受損時能為自己爭權的,本來就只有自己呀!可是,退一步來說:就算我願承擔不被信任的風險,我可能還是不敢講。
為什麼呢?
講了沒證據 ── 舉證門檻高
性侵害的發生往往只有被害人與加害人在場。而在排除數位性別暴力的情況下,僅存的實體證物(體液)在沒有主動檢驗的意識下,並不易被保存。
說白了,即使那年發生了好幾次,缺乏蒐證意識的我都沒留下任何證據。
因為,我在當下無法描述那種「感覺」。直到幾年後,我透過健教課才瞭解這是「性侵」。依據「無罪推定原則」,我知道,在缺乏有效證據的情況下,憑什麼都無法讓人相信我。
或許你認為:這絕對不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問題,而是天真的我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的問題。可是,退一步來說:就算我有證據,我可能還是不敢講。
為什麼呢?
講了被批判 ── 被冠上莫須有的責任
目前的我,不曾和能實際幫助我的體系求救過。
因為,就算他們相信我,我也不想面對諸如以下讓我不舒服的質疑:
「身為男性,你為什麼不保護好自己?你確定他不是跟你玩玩而已?」
在有毒的男子氣概 (toxic masculinity) 等遺緒的影響下,這種情況尤其容易發生在我這般的男性倖存者身上。
「你要講出來!才能幫到其他人。」
我瞭解,因應職務需求,他們需以結構視野、整體視角來處理議題。而身為倖存者,我們也當然樂見藉此累積改變的力量。然而,這樣子引導,就好像倖存者有「責」要救其他倖存者。但,真的嗎?
或許你認為:不要走心啊!別人只是一句話,幹嘛就這樣往心裡去。可是,退一步來說:就算我遇到的支持者十分友善,我可能還是不敢講。
為什麼呢?
講了更痛苦 ── 每講一次,就挖深一次傷痕
對多數倖存者來說。講,只有零次和無限次。
不論我們是想在當下透過司法流程討回公道,還是透過和各界揭露以促進他們對相關議題的重視,都是如此。
例如:我們可能會找醫師驗傷、社工師引導、警察做筆錄、檢察官調查、法官審問,或是監察院、民間團體的訪談計畫等。
獲得幫助,當然是值得感恩、惜福的事。但事實上,每講一次,我們就要主動回憶、重放那好幾段歷程一次。每講一次,就挖深一次傷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