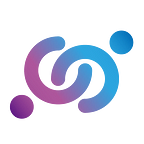從日治新文學到早期電影:臺灣研究的北美行旅
以台灣為研究主題這件事,意味著必須時時面對關於「台灣」的存在意義與知識定位的種種質疑。在北美進行台灣研究,除了文本語言及概念的轉譯外,同時也是針對學科意義和定位的再思考。北美的學術環境,為台灣研究帶來了哪些可能的論題與挑戰?而台灣研究又如何介入北美知識社群的討論與發展?
第十場【學人開講】由科技部人社中心張文薰執行委員主持,活動邀請美國Randolph-Macon College亞洲研究系的溫若含助理教授,分享她從台灣台文所的日治新文學訓練出發,到北美東亞系所研究殖民地早期電影的歷程,以及她對北美台灣研究的參與和觀察。
張文薰開場指出,當我們在台灣就學階段,研究台灣本地文本、關注台灣主體性如何建構,以及文本如何反應主體意識,可能是理所當然的事,但到了國外,究竟該如何與所屬的學術社群、教育機構、學生同儕等,說明台灣為何如此重要?因此邀請溫若含從就學經驗到工作狀況中,分享「從台灣海峽到全世界視野的台灣」。
自台大中文系、政大台文所、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亞洲語言及文化研究所,到目前任職的Randolph-Macon College 亞洲研究系,溫若含的人生歷程,或許也反映了(台灣研究)邊界不斷的變化。本次的講座由四個部分組成:
1.為什麼研究台灣?台灣研究在海外能做什麼?
2.教學現場(如何將台灣研究的思考帶進教學現場)
3.兩個研究案例(從自身角度出發,從電影、視覺文化,試圖回答核心問題)
4.北美地區的跨領域與跨媒介的知識社群分享。
首先第一部分就『為什麼研究台灣』,溫若含以侯孝賢的《悲情城市》一幕破題,電影中梁朝偉飾演的啞巴角色,面對本省人追打外省人的緊張情勢,努力擠出一句「我..是…台灣人」,這一幕不僅代表著台灣人的身份解決了角色當下的危機,溫若含認為這一幕同時展現出,台灣人身份一直都是不太確定的、光憑外表難以判斷台灣的意義。回到演講主題來看,溫若含提醒台灣研究是經歷許多海內外前輩的努力耕耘,從不同角度給予台灣位置、發言方式後,才逐漸成立的學科。而台灣研究的起源,可能就是起源自身份認同的危機(identity crisis)。
進一步解釋身份認同危機的意義,溫若含提到過去學者研究,指出台灣人意識的出現,是自日本殖民時期,因為被當成二等公民的情境,使得群體凝聚,試圖為台灣找出反殖民者的位置。爾後經歷冷戰、國共內戰,中華文化復興運動,瞬間轉變為大中華文化的代表,日治時期的作家再一次因為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的斷裂,再次經歷身份認同危機。而到了退出聯合國、中美斷交後,不再代表中國又再度衝擊台灣人的身份,繼而興起的新一波鄉土文學論戰,往後的原住民運動、新住民運動、多元性別運動等,都顯示台灣人不斷在經歷身份認同的變化。
直到現在身份認同也仍然是一個沒有穩定答案的問題,但溫若含表示:「沒有穩定答案不是壞事。在學術過程不斷去問,試圖從不同角度給解答,就是台灣研究的開始。」
演講來到第二部分,分享在教學現場的經驗,自身是如何試圖解釋「台灣是什麼」。第一個案例是李翰祥的《揚子江風雲》,作為一部間諜電影,其中有許多分別敵我的環節,其中一幕被視作漢奸的女性角色,是一位大家都搞不清楚他是誰的台灣人。溫若含解釋,「說不清楚的文化身份」,確實是在美國課堂上相對容易觸及學生的。原因是北美的多元文化情境,導致有很多學生自幼就在問「自己是誰」。所以從身份切入的台灣研究,能夠傳遞給學生關於「身份認同、是不是鐵板一塊、是不是固定的」的相關思考。
而另一種容易引導學生討論的議題,則是關於「成長、追溯過去的各種創傷」。萬仁1994年的《超級大國民》講述的是經歷白色恐怖後,獄中的政治犯釋放回家,訪問當年的朋友,想弄清楚發生過什麼事(為何入獄、朋友為何死亡)的一部電影。由於電影研究重視母題(motif),尋找畫面之間的共同點,溫若含選取電影中的三個畫面,其一是日本殖民時期,台灣人被派遣作為日本軍人到南洋或中國打仗,卻只有白骨回到台灣,幾個人圍成一圈盯著白骨哭泣的畫面。第二個畫面則是關押已久的主角從醫院醒來後,從主角視角看見大家盯著他看。第三個則是主角在騎樓看著櫥窗的畫面。張文薰回答自己對母題的想像,認為「這三個畫面的共通性就是非常用力在執行看的動作。」第一張是困惑的,疑惑著「白骨代表著死去的親人?」第二張則代表著政治犯釋放後,與家人格格不入的意思,同時表達著不只是家人疑惑主角「你是誰」,主角也疑問著家人「你是誰」。第三張則是主角不知道是在盯著櫥窗內的寵物看,或是看著入獄前無法想像的世界,抑或是看著玻璃窗上自身的倒影。
溫若含同意張文薰所提到的重點,一個關鍵是「你是誰」,點出身份也成為被觀看、被解釋的。主角不斷穿梭蜿蜒小巷,詢問的問題也難得到對的答案,揭示出身份問題其實很難有簡單的回答,答案實際上是會流動的。溫若含另舉Charles Yu所寫的Interior Chinatown(中譯《內景唐人街》 )一書為例,描述一個來自台灣,居住在美國中國城的移民家庭,家族隱約經歷過白色恐怖,但仍試圖找到正面的方式活下去,這部作品不斷挑戰主角的正面認知。最後在法庭的場合,給了很長的自白,試圖講清楚自己是誰。兩個案例都能夠對照學術界的關懷,溫若含解釋,實際在北美學界,陰影、移動經驗如何重新塑造認同,正是容易被認可的議題。所以台灣研究是能夠觸及「身份認同到底是不是固定?歷史創傷如何理解?移民經驗如何說清楚?」等許多與世界具有共通意義的議題。
溫若含另外補充自身對台灣研究很有用的思考方式,引述邱貴芬老師在處理台灣認同的形塑時的兩個重要觀點,一是抵抗權力中心(在權威論述經驗之外,移民社會、多元主義也是重要的,「挖掘典範之外的文化經驗,是多元的。」);二是拒絕一般反殖民主義的主張 — — 回歸純粹的論調(由於台灣本身為非常豐富的移民社會,只依賴西方的殖民、反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是不夠的,所以去想像一個可回歸的原點是有誤的。)張文薰表示贊同,並指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會注意到第一點,關注主流權威價值觀的作用,但主體性其實是ing的過程,因此張文薰提出「拒絕回歸純粹、原點,再去落實尊重多元,(接下來該去思考)可以藉由怎樣的方向、案例挖掘能做到?」
進入第三部分,溫若含分享他碩士班針對日治時期的新文學研究,以及博士班轉向影像,從影像角度思考文化的多元性可能。碩士班時期,溫若含找到電影史前史的「幻燈會」作為研究主題,當時日日新報在電影進入台灣後,就有報導「很酷很有趣,但跟幻燈會相似,不十分新奇。」電影在西方討論中,常被認為是新奇有趣的新媒介,但對於台灣而言,恰逢日本殖民之際,電影不只是新鮮的媒介,更被殖民政府當作教育工具使用。所以在溫若含的研究過程中,找到許多幻燈、電影放映的報導,都能看到電影被當成殖民教育的媒介。因此在台灣,電影不只是新奇的東西,更是一個能夠進入理論、思考現代性、具有權力關係的研究主題。此外,從媒介的觀點,若回到當時的殖民情境,日本政府展示殖民成果的展覽會上,幻燈會與活動寫真(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電影)同時在銀幕上被展現,也揭示出反進化論的可能性,也就是以往經常聽到「媒體在發展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有最受歡迎的媒介」,但當時同時並存著幻燈與電影兩項媒介並用。溫若含以媒體考古學觀點解釋,實際上透過媒體考古,也能看見許多與現在對應的思考方式,推翻了權威論述塑造的單線進化論,看到實際生命經驗都比單線歷史更加多元複雜。此外電影的使用也不僅僅是殖民政府的教育工具,同時民間的台灣文化協會也將幻燈、電影作為抵抗的教育工作,當時電影仍然沒有聲音概念,大多通過辯士,也被視作當時一種抵抗的代表。
至於影像思考的研究經驗分享,溫若含提到台灣研究中,很常探究的悲傷歷史,舉凡前述的電影都很常處理創傷、痛苦過程。近期的電影《幸福路上》,溫若含認為是以可愛的畫面談創傷。像是電影裡的粉紅色的霧,是父親上班的工廠所排放的廢氣,但在孩子眼中看見的是爸爸會帶著冰淇淋、棉花糖的甜美想像,「一方面讓你覺得很可愛,但同時也很可怕,有很多不愉快的東西夾雜在裡面。」而溫若含另外從電影製作的角度,回扣演講一開始的核心問題。導演起初嘗試找尋能代表台灣人的形象,但因動畫產業長期受到美日的影響,所以角色形象一開始不是太像好萊塢、迪士尼,就是太過日式動畫。
精彩演講以分享一些重要的研究學會、期刊、智庫以及社群為結束。張文薰延伸話題,提醒美國的複雜多元社會組成是值得台灣借鏡的,台灣經驗不只是個案,更具有普世性價值。溫若含表示由於任教學校是教育型的大學,課程類型較偏通識課程。有很多美國本地的學生,因為關心認同危機一事,想得知如何認識自己與他人,尤其在接觸其他文化時,由於很怕誤解對方而前來修課,希望了解如何從台灣角度看待台灣文化。另外有一部分學生,則是可能具有亞洲、台灣人的血統,因為電視與媒體的形象非常刻板,無法直接套用回生命經驗中,所以會在期末報告的撰寫過程中,感覺到自己身份有被討論的可能性。若由此層面來看,開設的課程便是為學生重新賦權。
在最後的Q&A環節有許多討論。與會者提問「台灣研究是否還有其他的研究面相?」溫若含回答,像是身份認同在性少數、性別多元的研究,非常值得投入,還有像是環境的議題,其實在台灣就有許多關於土地、環境的各種思考,永續生態也是在學術界經常看到的議題。另外還有不同的媒介、移民、非人文學者的研究領域也都值得發展。張文薰則表示,像是身份認同還能進一步討論,「在成為台灣人之前,我不能先是原住民嗎?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,那個台灣人是哪些人?有沒有看到原住民、新住民、精神障礙者的存在?歷史創傷又是哪一條歷史?」種種問題都仍需要官方與民間去共同思考。
另外的提問則是針對悲情城市畫面的提問,與會者詢問「(是不是在隱喻)不得不作politically correct表態?」溫若含表示同意,並進一步指出很多文藝創作者試圖描述的情境,並非要談論立場是什麼,而是描述在歷史情境裡,人們的困惑、暫時還說不清楚的狀態。還有與會者提到:「我們如何更全面地了解台灣被殖民的主體的『抵抗』為何?被殖民主體何以『抵抗』?如何與中國、日本等等地區的權力關係進行協商?我們如何理解日治時期被殖民台灣的模糊性和難以被定義(或者說,更積極地說,拒絕被定義)」,溫若含回覆「我的抵抗方式就是去找是不是有主流講的不一樣的東西。」,並解釋殖民現代性的問題,仍然需要許多時間、故事去闡述,當下情境下可能不只存在著抵抗,還有許多不得不活下去,而做出的各種反應。張文薰則指出,這問題需要以個案來討論,並以陳培豐《歌唱台灣》為例,過去我們經常想像台灣流行歌充滿很多悲情女性,流浪的漂泊的歌詞內容,是在反應台灣的多重殖民政權處境下,台灣人的悲哀。而陳培豐透過關照流行歌產業成立的物質條件,更細微的看見台灣跟日本人族群的互動變化,因此更能夠重新建構「抵抗」,看到自己的形象的認知。
並有提問「辯士與幻燈有關嗎?是否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?」溫若含回應確實相關,並提示過去研究的限制,由於殖民政府擁有更多資源能夠使文獻留到後代,是以現今所能看到的資料多是採取殖民政府的角度所記錄。如果有更多的資料,或許能夠進一步證明幻燈、電影不只有教化功能,而可能用於上層階級的娛樂、日本官僚的交流會等。
本活動歡迎報導或轉載紀錄,惟基於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之尊重,請事先聯繫本中心以取得授權同意,謝謝配合!